我叫杨保章,城郊乡上庄村人,今年65岁。在红旗渠即将迎来她通水50周年之际,作为一名林州人,我感到无比自豪。因为我也曾参加过修建红旗渠,红旗渠的渠岸上记载着我青春的足迹、浸染着我辛勤的汗水。
我常常向同事、朋友讲述修渠时发生的故事,他们感到很惊奇,感到不可思议:“你也到红旗渠总干渠劳动过,那时你才几岁呀,怎么会修红旗渠呢?”
重回故地
今年春节过后,我曾先后两次回到当年的修渠工地,寻找昔日修渠的印迹,回忆过去的峥嵘岁月,感悟自力更生、艰苦创业的红旗渠精神。
正月初五,大年还未过完,我在家人的陪同下,驱车赶到任村镇阳耳庄村——我当年修渠战斗过的地方。沿着蜿蜒曲折的阳耳庄至盘龙山公路,来到了红旗渠岸上。站在山头上,红旗渠如一条巨龙在半山腰回环盘旋,煞是壮观。踩着太行山花岗岩砌成的坚硬宽厚的渠岸,我找寻着昔日的一些印记。虽然经过50多年的风雨侵蚀,但“城关公社上庄营”的石刻依然清晰可见。看着渠水欢快地流淌,我的心里有说不出的舒畅。我在渠岸上整整徘徊了三个多小时,久久不愿离去。
3月6日,时令已是惊蛰,我又和老乡、原安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高福生等人来到阳耳庄村。惊蛰遍地开,山乡春来早。渠边的柳树早已换上了新装,柳枝随风飘舞。渠下的梯田内,是一小块一小块绿油油的青菜。仰望山上,50多年前的采石场还依稀可见,耳畔仿佛还听得见轰隆隆的炮声。昔日的驸马祠堂哪里去了?沿着山路向上走去,突然发现了一处雄伟壮观的碑林,听人介绍,这就是杨氏祠堂。我重新走在渠岸上,看着波光粼粼的渠水,记忆的闸门瞬间打开,修渠的点点滴滴,如电影一样一幕幕呈现在眼前。
初上工地
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,刚满十四周岁还在林县一中上学的我,利用暑假期间,顶替生病的父亲出工去修红旗渠。那天早上,母亲为我做了小米稠饭,还专门为我烙了熟红薯掺白面的油饼做干粮。从我家城关公社上庄村,到任村公社阳耳庄村大约70华里。我是第一次出远门,早上出发,赶到修渠驻地时,太阳已经落山了。我的腿直打哆嗦,站不起来,脚一着地便揪心般的疼痛,脱下鞋一看,双脚磨了好几个大水泡。
驻地离修渠工地大约500米,上工时每个民工都得从山脚下背着沙或水泥等材料,装袋子的叔叔看我年龄太小,有意给我少装了一锹沙,我便狠狠地瞪了他一眼:“咋了,小瞧我!”谁知上山还没走一半路,我便气喘吁吁地走不动了,只好走几步歇一会。沙袋在两个肩上来回倒腾。等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赶到工地时,大队民兵营长贺用山来到我的面前,瞪着牛眼珠般的大眼睛,满脸络腮胡子看不出表情,瓮声瓮气地说:“小保章,你不好好读书,来这儿受这罪干什么?你看这里哪有你干的活,趁早回去吧!”我低着头很委屈地说:“放暑假了,我爹病了不能出工,我来替俺爹。”正在这时,身高体壮的邻居义德叔赶紧走到我面前,对营长说:“小孩已经来了,就让他同我一组推石头吧,干几天不行再说。” 贺营长点了点头,我高兴得扭头就跑。突然一声“回来”,又让我愣在了原地,这时的贺营长已经没有了凶神恶煞的模样,到我跟前慈祥地说:“孩子,在山上和石头打交道,要多长个心眼,一定注意安全,收工时晚回去一会儿,看有没有丢下工具,顺便把咱大队的红旗扛回去,第二天再扛上山来。工分不少给你。”我听罢感激地向他鞠了一躬,心里乐滋滋地干活去了。
当时修渠实行半军事化管理,全县设总指挥部,公社设分指挥部,大队以营为单位,生产队是一个排,三个排为一个连,上下工听军号指挥。这样做的目的,主要是为了减少修渠或采石头放炮带来的危险。
修渠的工序比较简单,先有公社组织爆破组,把山上的石头炸下来,然后按民兵营修打成长方形或正方形的石块,再由民工从石料场,用小推车将石块运到红旗渠旁,完成第一道备料工序。第二道工序是垒砌渠岸,即民工在石缝中刨出土,掺上石灰和成泥,用铁锨送到砌石匠指定的位置。这时,两个抬石头的人,用木杠和铁链把石头一块一块地抬到匠人跟前,匠人将大小不等但比较规则的石块砌成渠岸墙。当时的水泥非常珍贵,只能把各石块间的缝隙扣条小缝。把沙及水泥和成水泥灰,填满小缝与石块齐平。这样既防止渠岸渗漏坍塌,又可保证渠内水流畅通。为了保证工程质量,便于追究责任,我们民兵营在修成的渠岸顶刻上“城关公社上庄营”的字样,并用箭头标示修渠距离。几个看上歪歪扭扭很不起眼的小字,折射出红旗渠成为世界奇迹的硬道理。
“洋学生”轶事
我参加修渠的时候,我们国家已经度过了1960年自然灾害,吃饱肚子不成问题,但由于劳动强度大,干活时间长,吃罢晚饭,我便像泥一样瘫在了铺上,夜里有尿也憋不醒,连续几天都尿在了褥子上。我怕丢人,起床后便不叠被子。房东大娘知道后,每天都悄悄的帮我把褥子晒干,还特意告诉邻铺,晚上要把我叫醒撒尿。邻铺说:“别说叫了,推他、扯耳朵都不醒,我真没法了。”大娘说:“看你笨的,捏住鼻子不就把他憋醒了”。
一个星期以后,我便适应了过度的劳累,晚上可以自己醒来撒尿了。晚饭后也能和工友到阳耳庄东边的小河边,洗洗脸、刷刷牙,在凉风习习的月光下朗诵一首古诗,或背诵一段俄语,有时还惹得民工一些议论:“这洋学生呜里哇啦地说些啥呀,这孩子能吃了修渠的苦,又肯学习,长大了肯定有出息。”记得有一天,下起了雨不能出工,民工们大都躺在被窝里睡懒觉,我悄悄地躲到一个叫驸马坟的祠堂里看小说。我陶醉在故事的情节中,不知不觉过了午饭时间,几个民兵排长在雨地里到处找我,淋得像落汤鸡似的。找到我后大家不但没有半句怨言,还鼓励我好好读书。炊事员崔大爷还特意为我备了一碗肉菜,放在灶火旁,说是下雨天改善生活,趁热吃了吧。我接过热气腾腾的饭菜,好长时间没有动筷子,一句话也说不出来,扑簌簌的两行热泪顺着脸颊流了下来。从此,“洋学生”的绰号便在工地上传开了。
山坡遇险
我所在的推石头组,每两人一个小推车,任务是把山顶上打造好的料石推到半山腰的渠岸边。装上石头往下推时叫重车,卸了车往上推时叫轻车,重车和轻车两人轮流着推。由于我年龄小,个子矮,推重车根本就站不起来,只能上山时推轻车,下山时用绳子从车后拉着小推车减缓速度。有一天快下工时,李义德叔叔推车的刹车绳突然断了一根。小推车在陡峭的山路上快速地向山下冲去。前面不远处就是推石头的队伍,一场车毁人亡的悲剧即将发生!在这千钧一发之际,我看到有个大木桩插在山坡上,情急之中快速将拉绳在木桩上绕了半圈,车速猛地降了下来。由于惯性,小推车车头一歪,倒在了路旁,一场事故瞬间得以避免。我的脸吓得煞白煞白,瘫坐在木桩旁,呆呆看着木桩。
原来这是一个宣传牌,木桩碗口粗细,一米多高,迎山的上下两面削得平展展的,一面写着“重新安排林县河山”,一面写着“让高山低头、河水让路”。这个木桩平时不知看过多少遍,标语也读了无数次,可在我的心目中没有留下一点印记。自从这次事故后,我对木桩有了救命之恩的感觉。可是事故的阴影始终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。当天夜里,晚饭也没吃就躺下睡觉,由于惊吓,半夜发起高烧。当我从昏昏沉沉中醒来,发现是房东大娘在给我扎人中穴,还熬了一碗放了红糖的姜汤。贺营长、义德叔、还有公社的医生也都在场,正商量着明天把我送回家的事。我坚决不答应,坚持要挣工分替义德叔修车。贺营长安慰我说:“孩子,别难过,不想回家就留下来吧,但你必须写份检查,把事情的经过如实写出来。”
第二天,我又扛着旗来到了工地,与以往不同的是,我自作主张把城关公社上庄民兵营的红旗绑在了大木桩上,对着木桩和红旗,我跪下磕了三个响头,心中觉得轻松了许多。更令我想不到的是,我写的事故检查,不知道怎么变成了表扬稿很快在工地传开了。意思是修渠队伍中的“洋学生”急中生智避免了一场伤亡事故。
又过了几天,听说公社社长要来我们工地检查质量和进度。我当时不知道公社社长是多大的官,心想一定很牛吧,也许是戴眼镜穿中山装的学者。正在我想入非非时,一个民工模样的人走到我面前,用粗糙的满是老茧的手摸着我的头问:“你就是‘洋学生’吧?”我惊讶地说:“你怎么知道啊?”他把我拉到身边,用手按着我的头,在肩膀处比划了一下说:“你头上刻着字呢!我能认不出来吗?好好干吧,‘洋学生’,修成红旗渠,将来你们是受益最多的人。不信,50年后你再来看一看。”摸我头的民工笑眯眯地走后,大伙儿一下把我围了起来,议论纷纷:“‘洋学生’,你真了不起,才来几天,就让社长给表扬了,我们修了这么多年渠,还没给社长说过一句话哩。50年后再到这儿,可千万别忘了我们啊。”
一个月的工期很快结束了,除了砌石墙,所有工序我都干了一遍。回家时同样走了70里的路,可我一点也没累的感觉。一个月的时间与65个春秋相比虽然短暂,但林州人吃苦耐劳、淳朴善良的优秀品质,潜移默化地融进了我的血液中,让我受益终身,并激励我在日后的工作中努力奋进。 (杨保章 口述 陈广红 整理)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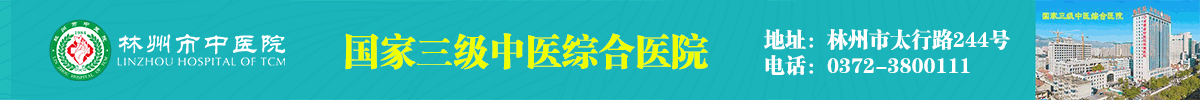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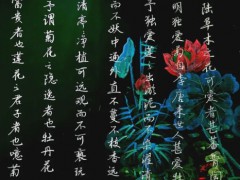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



 豫公网安备 41058102000016号
豫公网安备 41058102000016号